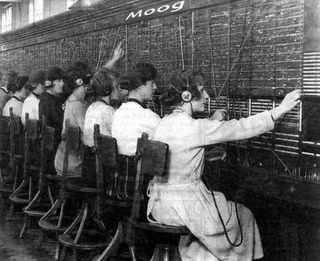永不

六四过了十六年,我才第一次走到街上。我一直觉得不上街不要紧,重要的是莫失,莫忘,记得,记着。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悼念方法,有的人喊口号,有的人舞动旗帜,有的人痛哭,有的人沉默,也有人为了那些逝去的人在“默默中揪心,一根头发渐渐变白“。只要不忘记 。
游行队伍的口号浪涛一般云涌而起,我混在好多人当中,从铜锣湾到中环,维园到政府总部,我连一句平反六四都没有说,我真的,没有说。四周卷起的潮骚样的律动,在两边刮出跌宕的版画的黑线条,浪潮转折的地方勾着像压抑的荇藻般咸腥的喘息,然后一路颠颠顿踬至我身边-------那些结束一党专政释放民运人士民主万岁宛如渗进黑鹤带体温的铁色羽毛-------声浪嘎然而止,如触礁一样。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要说我这种表现跟横额底下,干裂的嘴唇边的愤慨格格不入,我的木无表情是对那些神情哀伤的人们的背叛。那又怎样呢,对我没有买支联会的T恤我没有高举那些黑底白字的纸牌我没有抬着发泡胶制的民主女神边流汗边唱血染的风采,我好多好多都没有做,但我在队伍中间,我在里面走一步就说了一句话,是的,我患了中国人那种所谓内敛的遗传病,在公众场合尤其发作的厉害。如果有人要把我的沉默从我的肉骨剔出,我会说我对我的诉求很清楚,不需要口号的连连提醒。诉求很明确,因为我就在路上,队伍中间。被群体纳入吸收是危险的,但我今天不介意我作为个人的身份被模糊,成为“要求平反六四“的游行者之一员。
今天其实不是很热,但香港湿毒的天气,总是令人成身汗。纵我心静如柳下惠枯山水,明绿t恤却紧贴着我皮肤为我湿涟涟,我的身体执意奉迎毒日尘封的阴霾,坚决不肯自然凉。柏油路上的热气,点点聚,变成触角,躯干,带毛的四肢,小小的黑蚂蚁,潜进我的布鞋底。鞋面套桃红的手绣鸳鸯,在绿彩线培植的莲叶底下吐气。好湿。伏在莲叶鸳鸯下,平素最冷静的彩蓝,感染潮气后竟渐渐变成暖色,慢慢炖着菊花细火。
今天才知道,为了别人行,为了很多人行,跟很多人行,好累。
香港人很善忘,不知是否与天气有关。十六年前那天,我的父母坐在电视前,透过夜视镜的绿瞳看长安大街,我们听见炮火,爆出的火星,看不见流血,大人杜绝幻想和视线游溢至坦克轮带底下,爸爸妈妈把我和妹妹的疑问埋在默默无言里。荧幕切换着绿色与橙色,长安大街的灯亮了就是橙色,有人用手掌扑灭了灯,街就变了绿色。爸爸说橙色的街灯是用来防雾的,其实北京少有雾,听着哪,一支支高大的街灯,谁用来燃亮硝烟。那些目击的街灯,那时候有没有闭上无睫毛的秃眼睛,默许鲜血蜿蜒而过,填满天安门前的灰砖??第二天学校罢课,我们对着粗糙的油印纸唱爱自由为自由,真奇怪我那时怎么会唱普通话,学校都没有教。
那时我呢,二年级,七岁。回家看鬼马哺哺车的时候,哺哺车香蕉黄的车身传来枪声。达达达。
扣在浅蓝色的确凉校服的黑纱,乌蝶鳞一样轻,后来纱跌了,我在小吃部顾住买薯片没有去捡。初夏时香港有一百万人大游行,社会课本写着香港人口有六百多万,一百万人,即是,全香港,六个人,就有一个人在那队伍里。好多人。中环排到西环,几个地铁站。公益金百万行都没有那么多人。一路行一路行,涉着自己的汗水而过。哈。六月四日。我爸妈,现在一句都没有提。只是忙着搞离婚,在大陆开制衣厂,裁纸样,剪布。我都记得,你们怎么说忘了呢。
现在你怎么跟我说你们忘了呢。啊。咸丰年的事你提来把鬼。喂。世道艰难我地要揾食呀姐姐仔。游甚么行,赶住返屋企煮饭。目睹那么多年轻的生命流逝,你怎能跟我说,啊,那是。几时的事。
那些学生,如果他们没有举起横额,如果他们没有绝食,如果他们没有面对全副武装,如果他们不是生在中国,如果,如果,他们有多十六年,看着自己仔大女大,油烟把老婆的脸颊晕黄,腰间的皮肉在微小的平淡里滋长。如果,如果什么都没有用,如果任何行动只会换来绝望,如果,如什么果,其人已殁。
旺角街头展出六四的图片。脸的肌肉明明摆好了哭的姿势,可我一滴眼泪也没有,好像出嫁闭上眼等开脸,等哀伤以棉细的白线,把纤稀的淡黑的汗毛般的克制,沿雪白香粉摊开的路,片掉。哭十六年,水塘都流干,流入记忆的死海。
不少人都集中观看受害者血肉模糊的死状。其实不需要血腥的影象配合,整件事情都足以刺痛任何人,当然,前提是每一个人都有良知。我看见有几个十几岁的年轻人,挂一身鲜烈的颜色,对六四死难者的照片指手画脚,说咁核突咪睇啦我唔駛食飯。我真想。车她一巴掌。连基本的人道关怀都没有,这些人脱了一身潋滟的时尚,底下就是废物。
我对着那些坦克入城,空寂大街的照片,感到特别心痛,通明的首都盛满了虚空,华灯底下空无一人,像丢空的电影布景,演员全死掉,感觉又荒诞又荒凉。装甲车开走了,仗打完了,人人都输,有人输手手脚脚有人输民心有人输家人有人输命,赢的只有僵绿的铁皮。抹杀了人文的无机金属,宛如里面从来没有过人,有意识自生自灭随机地杀戮。面向镜子,在自己的毛孔稍大的脸上窥见清冷的玻璃下固态的水银。面对坦克,就看见在背面聚满柔润的宝石光泽,軟嫩的粉红石榴红内脏。
未必人人都要做烈士,甚至不一定要上街,喊口号,买支联会的胶手带。只要记得,起码在六月四日的时候,在物质与娱乐的甜头之间,记得,有很多人,普通人,用血来提醒我们自由是要争取,革命尚未成功。
走着的时候我跟伟棠说,在中国,烈士没有价值,用刀剑枪矛血汗消费希望,到最后志气消磨,花从梅萼落,然明春依旧韶光艳,漾如线。伟棠说有的。有他们的价值的。现在看不到。过了好多年后,会看到六四的价值的。中环竖满玻璃幕墙建就的图腾,对面行车线上车辆熟练地滑过,车上的乘客拿相机拍游行的队伍。汇丰和中银大厦外墙好象一面面大镜,却什么都照不到。我忽然有误入仙境的虚虚的感觉,足底的路面恍恍惚惚生出了有机的弹性。要不然就是世界误入了以脚步叠成的仙境,眼睛半开看着成群的人的出行,像凝视小小玻璃瓶里桅杆轻脆,白帆摆出受风的圆浑的鼓胀姿势的模型船。
然后我说。真嘎。
后记:去年十月路过长安街,时逢国庆,街上灯白如昼,硬生生挤出一个个皮笑肉不笑的假太阳,伪婵娟。无端的热情与喧闹压在黑夜上,黑夜就一点一点的断了呼吸,声声明如剪。谁还记得,十六年前。人人齐奔小康的步伐那么一致,怎复记那大街上,有几多双眼睛就此闭上。铛铛亮的皮鞋底下,经济收益的香甜里,谁还会理九里香之地,平凡的曾经的生生灭灭。
或者有人不再提起是因为恐惧,到一天恐惧的对象消失,他们便会开口,不过老实说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能等到那一天。可是更可怕的是麻木。不是不能提,不该提,不堪提,是“为什么要提?”